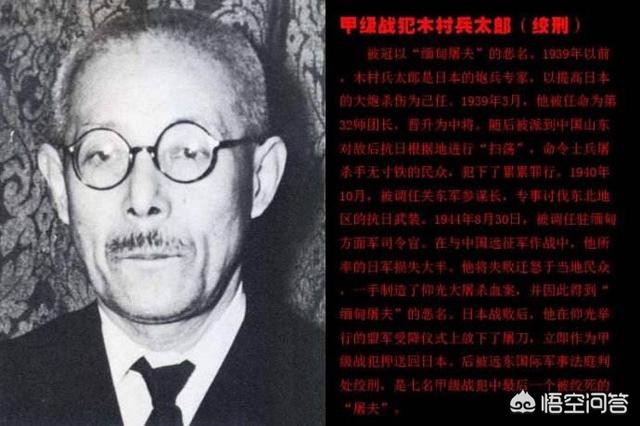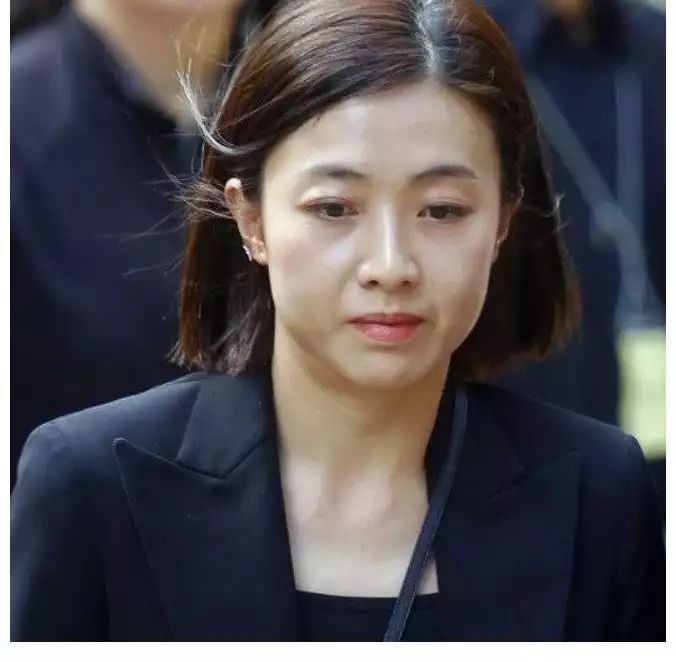夜晚的景色寂寞的老翁是一样的
- 时尚
- 2023-03-15
- 116
翁同龢晚景凄凉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膝下没有一儿半女。
其实,翁同龢是有家室的,20岁那年,他聚汤孟淑为妻,妻子比丈夫大一岁。遗憾的是,九年之后,汤孟淑因病去世。两年之后,翁同龢又遵照妻子的遗嘱,收纳汤孟淑的贴身婢女陆氏为妾。据说陆氏虽然相当勤快,却相貌丑陋,翁同龢不想违背亡妻的遗愿,才“按夫人遗嘱,立侍婢陆氏为妾”(《翁同龢日记·咸丰十年四月廿二日》)。陆氏虽比丈夫年轻十来岁,却也走在丈夫前面,而且没有生育。因此,人们往往认为翁某是“天阉”,即没有生育能力,不能行男女之事。据说翁同龢五十来岁时,一个不明底细的同僚到他府中拜访,劝他说:“您的爵位与声望都无与伦比,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儿女承欢膝下,为什么不聚一房妾,以延续祖宗的香火呢?”当时有不少仆役侍候在身边,翁同龢微微一笑,指着仆役们回答道:“我如果聚了妾,不是便宜了他们这班小子么?”顿时,主宾与众仆役都笑成了一团。
《红楼梦》中有“人生莫受老来贫”之说。“老来贫”是翁同龢晚景凄凉的又一个原因。
应该说,翁同龢还是比较清廉的。身为户部尚书,有一次他主持了向某国的贷款。事后,有关部门把一大笔回扣进献给他。翁同龢不但非常恼火地坚决拒绝,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光绪帝奏报了。光绪勃然大怒,立即派人秘密调查,凡是收受了回扣的,都准备严加惩处。然而,仅仅过了一天,当翁同龢再次见到光绪时,光绪却道:“昨天的事情,不必再追究了。”说完,一声长长地叹息:原来,慈禧太后也接受了回扣呢,这件事情,怎么可能再追究!身为帝党首领,翁同龢深受后党之忌。戊戌维新一开始,慈禧太后就找了个借口将他“开缺回籍”。临离开京城之际,直隶总督荣禄知道翁同龢相当贫困,就赠送给他白银千两,翁同龢坚决不肯接受,致使荣禄以为翁某与自己有嫌隙,因很不高兴而心存芥蒂。其实,翁同龢只是爱惜名誉,以此表示自己的清廉罢了。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时,翁同龢正任户部尚书,掌管国库银两划拨。由于翁同龢原本极力反对修建颐和园,承建颐和园的奸商李光昭为顺利从户部取得拨款,先是派人用重金向翁同龢行贿,被翁同龢大骂而出后,另辟蹊径,打听到翁同龢酷爱书法,便假装也是书法爱好者,将翁同龢与其父翁心存的书法编集成册,恭送给翁同龢过目。
翁同龢见到集子后果然大为高兴,于是乎,当李光昭提出需要采办南洋木材的款项时,翁同龢未加思索便应承下来。后来李光昭谎报木价、中饱私囊的事情败露,光绪帝大发雷霆,在电视连续剧《走向共和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,光绪帝质问他:“一本书法集,你翁师傅就把自己给卖了,还卖得这么贱?”当翁同龢辩解说李某是内务府推荐的,又有庆亲王的批文时,光绪打断他说:“李鸿章也找你要银子,还有朕的口谕,你怎么就不批给他呢?”当翁又标榜自己一生清廉、一时糊涂时,光绪毫不客气地反驳:“你是一生糊涂。名利名利,名在利前哪,翁师傅!”其时正是甲午战前,北洋舰队急需炮弹而李鸿章批不到银子,翁某却因一本书法集而把银子批给了奸商,应该说,翁某对甲午惨败负有一定责任:不逐利而追名,往往同样误国!
话说回来,翁同龢确实比较清廉,他在官场数十年,根本没有为自己大置房屋家产,以致丢了官职回到常熟老家时,只有薄田数顷——虽说没有子女,作为朝廷重臣,家中佣仆自然不会太少,因此,根本就不够开销。到了年残岁底,实在没办法了,就写信给侄儿翁曾桂,想向他借点银两。翁曾桂是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时,“一手挈之以起”,即完全靠着叔父的提携、栽培与照顾,才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。其时,翁曾桂已经官居浙江布政使,掌管浙江的财赋、民政等,这可是个大肥缺哟,而且,浙江省城杭州与常熟相距仅仅一天的路程。可是万没想到,翁曾桂接到信后,竟然不予回复。翁同龢气愤、懊恼至极,只得挑选几幅收藏的书画,再摘下朝服上挂缀的几颗珍珠,让家人送到当铺里,才算过了个年。后来,翁同龢穷困潦倒的境况传到了北京,他的不少门生故吏已经在京中官居要职、大富大贵了,大家便凑了一点银子,托翁同龢的同乡孙雄转交给他。这孙雄也是翁同龢的弟子,曾向翁同龢学习骈文,并协助他办理过笔札等。可是,孙雄竟然吞没了这些银子,根本就没有告诉翁同龢。翁同龢的书法早年从习欧阳洵、褚遂良、柳公权、赵孟頫,书法崇尚瘦劲;中年转学颜体,取其浑厚,又兼学苏轼、米芾,号称“乾嘉以后一人”(民国·徐珂《清稗类钞·艺术类》)。晚年免官家居时,不再慕学前人而任意挥毫,益显超逸潇洒。他喜欢吟诗赋词,就随手取纸片作草稿,日积月累,这些草稿他都整箱整捆地保留着。由于他曾是两朝帝师,又是朝廷重臣,再加上特别注重名誉,因此不可能像郑板桥那样卖字赚钱。而他去世之后,书法家的名声更大,一副楹联就价值20两银子。于是,留下的那些墨宝,渐渐地被家人们盗卖得差不多了。
精神上承受的巨大压力,也是翁同龢晚景凄凉的重要原因。
戊戌维新之初,他被“开缺回籍”,除了帝党与后党间明争暗斗的因素外,翁某确有“揽权”与“办事多不允协”(《清史稿·翁同龢传》)的责任。然而,当慈禧发动政变,软禁了光绪帝后,处置就严厉多了:“翁同龢著革职,永不叙用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常熟县令朱某乘机摆着“公事公办”的面孔,每天带着吏役上门骚扰,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得到翁某的墨宝而已,当翁同龢满足了他题屏风、书对联的要求后,骚扰势必减轻。然而,来自北京朝廷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翁的晚年。现代学者马叙伦在民国年间编撰的《石屋余渖》中,记载了翁同龢亲笔所书的《并未生事帖》:
“具禀
奉旨驱逐回籍,严加管束,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:
本月同龢在籍,并未滋生事端。”
文后尚有“云云”,说明翁某所书,还有一些并未录入。常熟县隶属于苏州府,翁同龢有个学生,是浙江仁和县人,名叫陆懋勋,他在担任代理苏州知府期间,曾亲手接到老师翁同龢的这种“禀呈”。常熟到苏州有一百多里,即使每月由家人或仆役呈送,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,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。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(1830)四月,光绪三十年(1904)年初,陪伴翁同龢40多年的妾陆氏病逝,翁同龢痛吟“已为朝政削官籍,又见妻妾隔幽冥”诗句,以寄托凄苦悲伤之情。同年五月,翁本人也溘然而逝,享年75岁。弥留之际,翁同龢还向守候于病榻前的亲属口占一绝:
“六十年中事,伤心到盖棺;
不将两行泪,轻与汝曹弹。”
这首五言绝句,似乎是给他从戊戌年(1898)罢官家居到驾鹤西行这整整六年间的凄凉晚景,作了一个注脚。